|
一申治病不明标本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二条)。凡病有标本,更有似标之本,似本之标。若不明辨阴阳逆从,指标为本,指本为标,指似标者为标,似本者为本,迷乱经常,倒施针药,医之罪也。
治病必求其本。
万事万变,皆本阴阳。而病机药性,脉息论治,则最切于此。故凡治病者,在必求于本,或本于阴,或本于阳,知病所繇生而直取之,乃为善治。若不知求本,则茫如望洋,无可问津矣。今世不察圣神重本之意,治标者常七八,治本者无二三,且动称急则治标,缓则治本,究其所为缓急,颠倒错认,举手误人,失于不从明师讲究耳。所以凡因病而致逆,因逆而致变,因寒热而生病,因病而生寒热者,但治其所生之本原,则后生诸病,不治自愈。所以得阴脉而见阳证者,本阴标阳也。得阳脉而见阴证者,本阳标阴也。若更治其标,不治其本,则死矣,为医而可不知求本哉?知标与本,用之不殆;明知逆顺,正行无间;不知是者,不足以言诊,足以乱经。故《大要》曰∶粗工嘻嘻,以为可知。言热未已,寒病复始,同气异形,迷诊乱经,此之谓也。
中道而行,无所疑问,不有真见,安能及此?粗工妄谓道之易知,故见标之阳,辄从火治;假热未除,真寒复起。
虽阴阳之气若同,而变见之形迥异,粗工昧此,未有不迷乱者矣。
百病之起,多生于本。六气之用,则有生于标者,有生于中气者。太阳寒水,本寒标热;少阴君火,本热标寒,其治或从本,或从标,审寒热而异施也。少阳相火,从火化为本;太阴湿土,从湿化为本,其治但从火湿之本,不从少阳太阴之标也。阳明燥金,金从燥化,燥为本,阳明为标;厥阴风木,木从风化。风为本,厥阴为标,其治不从标本而从乎中,中者中见之气也。盖阳明与太阴为表里,其气互逆于中,是以燥金从湿土之中气为治。厥阴与少阳为表里,其气互通于中,是以风木从相火之中气为治,亦以二经标本之气不合,故从中见之气以定治耳。若夫太阳少阴,亦互为中见之气者,然其或寒或热,标本甚明,可以不求之于中耳。至于诸病,皆治其本,惟中满及大小二便不利,治其标。
盖中满则胃满,胃满则药食之气不能行,而脏腑皆失所禀,故无暇治其本。先治其标,更为本之本也。二便不通,乃危急之候,诸病之急,无急于此,故亦先治之,舍此则无有治标者矣。至于病气之标本,又自不同。病发而有余,必累及他藏他气,先治其本,不使得入他藏他气为善。病发而不足,必受他藏他气之累,先治其标,不使累及本藏本气为善。
又如病为本,工为标,工不量病之浅深,病不择工之臧否,亦是标本不得也。缘标本之说,错出难明,故此述其大略云。
一申治病不本四时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五条)。凡治病,而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,所谓违天者不祥,医之罪也。
治不本四时。
不本四时者,不知四时之气,各有所本,而逆其气也。春生本于冬气之藏;夏长本于春气之生;长夏之化,本有夏气之长;秋收本于长夏之化;冬藏本于秋气之收。如冬气不藏,无以奉春生;春气不生,无以奉夏长;不明天时,则不知养藏养生之道,从何补救?逆春气,则少阳不生,肝气内变。又夏为寒变。
阳气不能鼓动而生出,内郁于肝,则肝气混揉,变而伤矣。肝伤则心火失其所生,故当夏令而火有不足,寒水侮之,变热为寒也。
逆夏气,则太阳不长,心气内洞。又秋为疟。
阳气不能条畅而外茂,内薄于心,燠热内消,故心中洞然而空也。心虚内洞,则诸阳之病作矣。心伤则暑气乘之,至秋而金气收敛,暑邪内郁,于是阴欲入而阳拒之,故为寒。火欲出而阴束之,故为热。金火相争,故寒热往来而为疟。
逆秋气,则太阴不收,肺气焦满。又冬为飧泄。
肺热叶焦,为胀满也。肺伤则肾水失其所生,故当冬令而为肾虚飧泄。飧泄者,水谷不分而寒泄也。
逆冬气,则少阴不藏,肾气独沉。又春为痿厥。
少阴主藏,少阴之气不伏藏,而至肾气独沉,则有权无衡,如冷灶无烟,而注泄沉寒等病作矣。肾伤则肝木失其所生,肝主筋,故当春令而筋病为痿。阳贵深藏,故冬不能藏,则阳虚为厥。此可见春夏生长之令,不可以秋冬收藏之气逆之。秋冬收藏之令,不可以春夏生长之气逆之。医者而可悖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之旨乎?
一申治病不审地宜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六条)。凡治病,不察五方风气,服食居处,各不相同,一概施治,药不中窍,医之过也。
治不法天之纪、地之理,则灾害至矣。
天时见上,地之寒、温、燥、湿、刚、柔,五方不同。人病因之,故《内经》以《异法方宜》名篇,可见圣神随五方风气,而异其法以宜民也。
东方之民,食鱼而嗜咸,鱼者使人热中,盐者胜血,故其民皆黑色疏理,其病皆为痈疡,其治宜砭石,故砭石者,亦从东方来。
鱼发疮,盐发渴,血弱而热,易为痈疡。
西方之民,陵居而多风,水土刚强,其民不衣而褐荐,华食而脂肥,故邪不能伤其形体,其病生于内,其治宜毒药。
故毒药者,亦从西方来。
水土刚强,饮食脂肥,肤腠闭封,血气充实,外邪不能伤。病生于喜怒思忧恐,及饮食男女之过甚也。
北方其地高,陵居风寒冰冽,其民乐野处而乳食,藏寒生满病,其治宜灸,故灸者,亦从北方来。
水寒冰冽,故生病于藏寒也。
南方其地下,水土弱,雾露之所聚也,其民嗜酸而食,致理而赤色,其病挛痹,其治宜微针,故九针者,亦从南方来。
食所食不芬香也,酸味收敛,故人皆肉理密致。阳盛之处,故色赤。湿热内淫,故筋挛脉痹也。
中央地平以湿,民食杂而不劳,故其病多痿厥寒热,其治宜导引按跷,故导引按跷者,亦从中央出也。
东方海,南方下,西方北方高,中央之地平以湿,地气异,生病殊焉。
圣人杂合以治,各得其所宜,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,得病之情,知治之大体也。
随五方用法,各得其宜,惟圣人能达其性情耳。
春气西行,夏气北行,秋气东行,冬气南行。故春气始于下,秋气始于上,夏气始于中,冬气始于标。春气始于左,秋气始于右,冬气始于后,夏气始于前,此四时正化之常,故至高之地,冬气常在;至下之地,春气常在,必谨察之。
地有高下,气有温凉,高者气寒。下者气热。故失寒凉者胀,失温热者疮,下之则胀已,汗之则疮已,此腠理开闭之常,大小之异耳。西北之气,散而收之;东南之气,收而温之,所谓同病异治也。故曰气寒气凉,治以寒凉,行水渍之;气温气热,治以温热,强其内守,必同其气,可使平也。假者反之,崇高则阴气治之,污下则阳气治之,高者其人寿,下者其人夭。
一申治病不审逆从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二条)。凡治病有当逆其势而正治者,有当从其势而反治者,若不悬鉴对照,而随手泛应,医之罪也。
不审逆从不审量其病,可治与不可治也。
逆从倒行,反顺为逆也。
逆从者,以寒治热,以热治寒,是逆其病而治之。以寒治寒,以热治热,是从其病而治之。从治即反治也。逆者正治,辨之无难。从者反治,辨之最难。盖寒有真寒假寒,热有真热假热,真寒真热,以正治之即愈。假寒假热,以正治之则死矣。假寒者,外虽寒而内则热,脉数而有力,或沉而鼓击,或身寒恶衣,或便热秘结,或烦满引饮,或肠垢臭秽,此则明是热极,反兼寒化,即阳盛格阴也。假热者,外虽热而内则寒,脉微而弱;或数而虚;或浮大无根;或弦芤断续,身虽炽热而神则静,语虽谵妄而声则微,或虚狂起倒,而禁之则止;或蚊迹假,而浅红细碎;或喜冷水而所用不多;或舌胎面赤而衣被不撤;或小水多利;或大便不结,此则明是寒极,反兼热化,即阴盛格阳也。假寒者清其内热,内清则浮阴退舍矣。假热者温其真阳,中温则虚火归元矣,是当从治者也。凡用奇偶七方而药不应,则当反佐以入之。
如以热治寒而寒格热,反佐以寒则入矣。如以寒治热而热格寒,反佐以热则入矣。又如寒药热服,借热以行寒;热药寒服。借寒以行热,皆反佐变通之法,因势利导,故易为力,亦小小从治之意也。
一申治病不辨脉证相反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九条)。凡治病,不辨脉与证之相反,懵然治之,医之罪也。或不得已,明告而勉图其难,则无不可。
气虚身热,此谓反也。
阳气虚,则不当身热而反热,身热则脉气当盛而反虚,是病气与证不符,故谓反也,反则胡可妄治。
谷入多而气少,此谓反也。
谷入于胃,助其胃气,散布经络,当充然有余,今谷入多而气少,是胃气不布也。
谷不入而气多,此谓反也。
胃气外散,脉并之也。
脉盛血少,此谓反也。脉少血多,此谓反也。
经脉行气,络脉受血,经气入络,络受经气,候不相合,故皆反常。
谷入多而血少者,得之有所脱血,湿居下也。
脱血则血虚,血虚则气盛,盛气内郁,逼迫津液,流入下焦,故云湿居下也。
谷入少而气多者,邪在胃及与肺也。
胃气不足,肺气下流于胃中,故邪在胃。然肺气入胃,则肺气不自守,气不自守,则邪气从之。故云邪在胃及与肺也。
脉小血多者,饮中热也。
饮留脾胃,则脾气溢,脾气溢,则发热中。
脉大血少者,肺有风气,水浆不入。
风气盛满,则水浆不入于脉。
形盛脉细,少气不足以息者危。形瘦脉大,胸中多气者死。
合此一条观之,前四条皆危证。然脉细少气者危,脉大多气者死,又与损至之脉同推矣。
一申治病不察四易四难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二条)。凡治病,参合于望色切脉审证三者,则难易若视诸掌。粗工难易不辨,甚且有易无难,医之罪也。
凡治病,察其形气色泽,脉之盛衰,病之新故,及治之无后其时。形气相得,谓之可治;色泽以浮,谓之易已;脉从四时,谓之可治;脉弱以滑,是有胃气,命曰易治。
气盛形盛,气虚形虚,是相得也,故可治。气色明润,血气相营,故易已。春弦夏钩,秋浮冬沉,顺从四时,故可治。弱而且滑,胃气适中,无过不及,故易治。
形气相失,谓之难治;色夭不泽,谓之难已;脉实以坚,谓之益甚;脉逆四时,为不可治,必察四难而明告之。
形与气两不相得,色夭枯而不明润,脉实坚而无胃气,逆四时而脉反常,此四者工之所难为,故必明告之,粗之所易治,曾不加察也。
一申治病不察新久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六条)。凡治病,不辨新病邪实,久病正虚,缓急先后失序而实实虚虚,医之罪也。
征其脉小,色不夺者,新病也。
气乏而神犹强也。
征其脉不夺,其色夺者,此久病也。
神虽持,而邪则凌正也。
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,此久病也。
神与气俱衰也。
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,新病也。
神与气俱强也。新病可急治,久病宜缓调。
五脏已败,其色必夭,夭必死矣。
色者神之旗,藏者神之舍,神去则藏败,藏败则色见夭恶。
故病久则传化,上下不并,良医弗为。
病之深久者,变化相传,上下气不交通,虽医良法妙,亦何以为之。
一申治病不先岁气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四条)。凡治病,不明岁气盛衰,人气虚实,而释邪攻正,实实虚虚,医之罪也。
不知年之所加,气之盛衰,虚实之所起,不可以为工矣。
不知岁运之盛衰,自不知人气之虚实,失时反候,五治不分,邪辟内生,工不能禁也。
不知气之至与不至,而失其时,反其候,则五运之治,盛衰不分。其有邪辟内生,病及于人者,虽医工莫能禁之,繇其不知时气也。
不知合之四时五行,因加相胜,释邪攻正,绝人长命。
不知邪正虚实,而妄施攻击,夺人真元,杀人于冥冥之中,故为切戒。
必先岁气,无伐天和。无盛盛,无虚虚,而遗人夭殃,无致邪,无失正,绝人长命。
《内经》谆谆示戒,学人可不求师讲明。盖岁有六气,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,先知此六气所在,人脉至尺寸应之。
太阴所在,其脉沉;少阴所在,其脉钩;厥阴所在,其脉弦;太阳所在,其脉大而长;阳明所在,其脉短而涩;少阳所在,其脉大而浮。如是六脉,则谓天和,不识者,呼为病脉。攻寒令热,脉不变而热疾已生。制热令寒,脉如故而寒病又起,欲求其适,安可得乎?夭枉之来,率繇于此,不察虚实,但用攻击,盛盛虚虚,致邪失正,遗人夭殃,绝人长命也。
北政之岁,少阴在泉,则寸口不应;厥阴在泉,则右不应;太阴在泉,则左不应。南政之岁,少阴司天,则寸口不应;厥阴司天,则右不应;太阴司天,则左不应,诸不应者,反其诊则应矣。北政之岁,三阴在下,则寸不应;三阴在上,则尺不应。南政之岁,三阴在天,则寸不应;三阴在泉,则尺不应,右左同。
一申用药不远寒热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一条)。凡治病,用寒远寒,用热远热,其常也。不远寒热,其变也。若不知常变,一概施治,酿患无穷,医之罪也。
发表不远热,攻里不远寒。不发不攻,而犯寒犯热,寒热内贼。其病益甚。故不远热则热至,不远寒则寒至,寒至则坚否、腹满、痛急下利之病生矣。热至则身热、吐下、霍乱、痈疽、疮疡、瞀郁、注下、、肿胀、呕、鼽衄、骨节变、肉痛、血溢、血泄、淋之病生矣。
治病惟发表不远热,非发表则必远热矣。惟攻里不远寒,非攻里则必远寒矣。不当远而远,当远而不远,其害俱不可胜言。
一申治病不知约方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二条)。凡用方,不分君臣佐使,头绪纷杂,率意妄施,药与病迥不相当,医之罪也。
约方,犹约囊也。囊满弗约,则输泄。方成弗约,则神与弗居。
业医者,当约治病之方,而约之以求精也。《易》曰∶精义入神,以致用也,不得其精,焉能入神?有方无约,即无神也,故曰神与弗居。藏位有高下,府气有远近,病证有表里,用药有轻重。调其多少,和其紧慢,令药气至病所,故为勿太过与不及,乃为能约。
未满而知约之可为工,不可以为天下师。
未满而知约,何约之有?是以言约者,非满不可,故未满而知约,必不学无术之下材耳。然较诸全不知约者,失必稍轻。尝见用峻剂重剂之医,屡获奇中;及征其冥报,比用平剂、轻剂者转厉,岂非功以幸邀,不敌罪耶?噫!安得正行无间之哲,履险皆平,从权皆经也哉?
一申治病不知约药之律
(律一条发明《内经》二条)。凡用药太过不及,皆非适中,而不及尚可加治,太过则病去药存,为害更烈,医之过也。
帝曰∶有毒无毒,服有约乎?岐伯曰∶病有久新,方有大小,有毒无毒,固宜常制矣。大毒治病,十去其六;常毒治病,十去其七;中毒治病,十去其八;无毒治病,十去其九;谷肉果菜,食养尽之,无使过之,伤其正也。
下品烈毒之药治病,十去其六即止药;中品药毒次于下品治病,十去其七即止药;上品药毒,毒之小者,病去其八即止药;上下中品,悉有无毒平药,病去其九即当止药,此常制也。
有毒无毒,所治为主,适大小为制也。
但能破积愈疾,解急脱死,则为良方。非必以先毒为是,后毒为非,无毒为非∶有毒为是,必量病轻重大小而制其方也。《周礼》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,以无毒之药可以养生,不可以胜病耳。今世医人通弊,择用几十种无毒之药,求免过愆。病之二三,且不能去,操养痈之术,坐误时日,迁延毙人者比比,而欲己身长享,子孙长年,其可得乎?
一申治病不疏五过之律
(律一条释《经》文五条)。凡诊病,不问三常,不知比类,不察神志,不遵圣训,故犯无忌,医之过也。
凡未诊病者,必问尝贵后贱,虽不中邪,病从内生,名曰脱营。尝富后贫,名曰失精。五气留连,病有所并。粗工诊之,不在脏腑,不变形躯,诊之而疑,不知病名。身体日减,气虚无精,病深无气,洒洒然时惊病深者,以其外耗于卫,内夺于营,良工所失,不知病情,此亦治之一过也。
过在不问病情之所始也。
凡欲诊病者,必问饮食居处。暴乐暴苦,始乐后苦,皆伤精气,精气竭绝,形体毁沮,暴怒伤阴,暴喜伤阳,厥气上行,满脉去形。愚医治之,不知补泻,不知病情,精华日夺,邪气乃并,此治之二过也。
过在不知病患七情所受,各不同也。
善为脉者,必以比类奇恒,从容知之。为工而不知道,此诊之不足贵,此治之三过也。
比类之法,医之所贵。如老吏判案,律所不载者,比例断之,纤悉莫逃也。奇恒者,审其病之奇异平常也。从容者,凡用比类之法,分别病能。必从容参酌,恶粗疏简略也。
诊有三常,必问贵贱,封君伤败,及欲侯王,故贵脱势,虽不中邪,精神内伤,身必败亡。始富后贫,虽不中邪,皮焦筋屈,痿为挛。医不能严,不能动神,外示柔弱,乱至失常,病不能服,则医事不行,此治之四过也。
此过繇于不能戒严病者,令之怀然神动,蠲除忧患,徒外示柔弱,委曲从人也。
凡诊者,必知终始,有知绪余。切脉问名,当合男女,离绝菀结,忧恐喜怒,五脏空虚,五气离守,工不能知,何术之语?察气色之终始,知病发之余绪。辨男女之顺脉,与七情内伤,故离间亲爱者魂游;绝念所怀者意丧;菀积所虑者神劳;结固余怨者志苦;忧愁者闭塞而不行;恐惧者荡惮而失守;盛怒者迷惑而不治;喜乐者惮散而不藏。由是八者,故五脏空虚,血气离守,工不思晓,又何言医?尝富大伤,斩筋绝脉,身体复行,令泽不息,故伤败结,留薄归阳,脓积寒热。粗工治之,亟夺阴阳,身体解散,四肢转筋,死日有期,医不能明,不问所发,惟言死日,亦为粗工,此治之五过也。
非分过损,身体虽复,津液不滋;血气内结,留而不去,薄于阳脉,则化为脓;久积腹中,则外为寒热也。不但不学无术者为粗工,即使备尽三世经法,而诊不辨三尝,疗不慎五过。亦为粗略之医也。
凡此五者,受术不通,人事不明也。
一申治病不征四失之律
(律一条明录经文二条)。凡治病,不问证辨脉,而以无师之术笼人,此最可贱,不足罪也。
夫经脉十二,络脉三百六十五,此皆人之所明知,工之所循用也,所以不十全者,精神不颛,志意不理,外内相失,故时疑殆。
精神不颛,不能吉凶同患。志意不理,不能应变无穷。内外相失,不能参合色脉,安得不疑而且殆?诊不辨阴阳,此治之一失也。受师不卒,妄作杂术,谬言为道,更名自功,妄用砭石,后遗身殃,此治之二失也,不适贫富贵贱之居,坐之浓薄,形之寒温,不适饮食之宜,不别人之勇怯,不知比类,足以自乱,不足以自明,此治之三失也。诊病不问其始,忧患饮食之失节,起居之过度,或伤于毒,不先言此,卒持寸口,何病能中?妄言作名,为粗所穷,此治之四失也。
申明仲景律书
(附杂证时病药禁一条附伤寒三阳经禁一条)。
原文允为定律,兹特申明十义,不更拟律。
一申治风寒不可发汗之律
伤寒有五,皆热病之类也。同病异名,同脉异经,病虽俱伤于风,其人素有锢疾,则不得同法。其人素伤于风,因复伤于热,风热相搏,则发风温,四肢不收,头痛身热,常汗出不解。治在少阴厥阴,不可发汗。汗出语独语,内烦躁扰不得卧,善惊,目乱无精,治之复发其汗,如此死者,医杀之也。
伤寒有五,即伤寒、中风、风温、湿温、疫疟也。寒风温热凉各别,素有锢疾,不得同法。即动气在上下左右,不可汗下之类,伤风重复伤热,两邪相搏于内。本属少阴里证,如温疟之病,而厥阴风木,则兼受之,热邪充斥两脏,尚可用辛温发散助其疟乎?误发其汗,死证四出,不可复救矣。复发其汗,即申上文不可发汗者。复发其汗,非是死证已出,复发其汗也。
一申治湿温不可发汗之律
伤寒湿温,其人常伤于湿,因而中,湿热相搏,则发湿温。病苦两胫逆冷,腹满叉胸,头目痛,苦妄言。治在足太阴不可发汗,汗出必不能言,耳聋,不知痛所在,身青面色变,名曰重。如此者死,医杀之也。
湿温即暑与湿交合之温病,素伤于湿,因复伤暑,两邪相搏,深入太阴,以太阴主湿,召暑而入其中也。两胫逆冷腹满,湿得暑而彰其寒。叉胸、头目痛、苦妄言,暑得湿而彰其热,此但当分解热湿之邪,而息其焰,宁可发汗,令两邪混合为一耶?发汗则口不能言,耳不能闻,心不知苦,但身青面色变,显露于肌肉之外耳。病而至重,又非虚虚实实之比,直为医之所杀矣。二律出《脉经》,王叔和集医律之文,然则医律古有之矣,何以后世无传耶?详考仲景以前,冬月之伤寒尚未备,况春月之风温,夏月之湿温乎?是则医律为仲景之书无疑矣,盖《伤寒论》全书皆律,其书中不及载之证,另作律书以纬之。传至晋代,伤寒书且得之搜采之余,而律书更可知矣。所以叔和虽采二条入《脉经》,究竟不知为何时何人之言也。再按律书虽亡,而三百九十七法具在,其法中之律,原可引伸触类,于以神而明之。如曰此医吐之过也,此医下之所致也,与夫不可汗,不可下,不可火,不可用前药,此为小逆,此为大逆,此为一逆再逆,此为难治,此为不治,条例森森,随证细心较勘,自能立于无过。兹将脉法中大戒,发明数则,俾察脉之时,预知凛焉。
一申治伤寒病令人亡血之律
病患脉微而涩者,此为医所病也。大发其汗,又数大下之,其人亡血,病当恶寒,后乃发热,无休止时。夏月盛热,欲着复衣。冬月盛寒,欲裸其体。阳微则恶寒,阴弱则发热,此医发其汗,令阳气微,又大下之,令阴气弱。五月之时,阳气在表,胃中虚冷,以阳气内微,不能胜冷,故欲着复衣。十一月之时,阳气在里,胃中烦热,以阴气内弱,不能胜热,故欲裸其身,又阴脉迟涩,故知亡血也。
人身之脉,阴阳相抱,荣卫如环。伤寒病起之后,脉见阳微阴涩,知为医之所累,大汗大下,两伤其荣卫,以故恶寒发热无休止时,乃至夏月反毗于阴,冬月反毗于阳。各造其偏,经年不复,其为累也大矣,即阳脉之微,以久持而稍复,而但阴脉迟涩,亦为亡血,以阴血更易亏难复耳,设其人平素脉微且涩,医误大汗大下,死不终日矣。此论病时汗下两伤,所以经年不复之脉也。
一申治伤寒病令人发KT之律
寸口脉浮大,医反下之,此为大逆。浮为无血,大即为寒,寒气相搏,即为肠鸣。医乃不知,而饮水令大汗出,水得寒气,冷必相搏,其人即KT。
寸口脉浮大,病全在表。医反下之,则在表之阳邪下陷,而胃中之真阳不治,遂成结胸等证,故为大逆。浮主气,故曰无血,即浮为在表,未入于阴之互辞。大即为寒,见外感之邪,全未外解也。中有一证,下陷之邪,与藏气相搏而为肠鸣者,此必未尝痞结至极,盖痞结即不复转气也。医不知其人邪已内陷,当将差就错,内和其气,反饮水令大汗出,是下之一损其胃中之阳,饮水再损其胃中之阳,腹中之邪,随汗出还返于胃,与水气相搏,且夹带浊气,上干清气,其人即KT。KT者胃气垂绝之象,伤寒之危候也。然其死与不死,尚未可定。盖脉之浮大,本非微弱之比,而邪之内陷,当大逆者,止成肠鸣小逆。倘发KT已后,阳气渐回,水寒渐散,仍可得生。观后条仲景谓寒聚心下,当奈何也?此则聚而不散,无可奈何,仁人之望绝矣。
一申治伤寒病致人胃寒之律
寸口脉濡而弱,濡即恶寒,弱即发热,濡弱相搏,藏气衰微,胸中苦烦,此非结热,而反薄居。水渍布冷铫贴之,阳气遂微,诸府无所根据,阴脉凝聚,结在心下而不肯移。胃中虚冷,水谷不化,小便纵通,复不能多。微则可救,聚寒不散,当奈何也!此见寸口阳脉濡,阴脉弱,乃藏气素衰之征。阳濡则恶寒,阴弱即发热。其人胸中苦烦,即为虚烦,不当认为结热,而以水渍布冷贴,重伤其胸中之阳也。盖胸中之阳,为诸府之所根据籍,阳气一微,阴气即凝结心下,如重阴蔽,胃中水谷,无阳以化,而水寒下流。小便纵宣通,然阳不化气,复不能多,履霜坚冰,可奈何耶?亦因平素脉之濡弱,知其胸中之阳,不能复辟耳。
一申治伤寒病遇壮盛人发汗过轻之律
寸口脉洪而大,数而滑。洪大则荣气长,滑数则卫气实。荣长则阳盛拂郁,不得出身;卫实则坚难,大便则干燥,三焦闭塞,津液不通。医发其汗,阳气不周,重复下之,胃燥干蓄,大便遂摈,小便不利。荣卫相搏,心烦发热,两眼如火,鼻干面赤,舌燥齿黄焦,故大渴。过经成坏病,针药所不能制,与水灌枯槁,阳气微散,身寒温衣复,汗出表里通,然其病即除,形脉多不同。此愈非法治,但医所当慎,妄犯伤荣卫。
此见荣卫强盛,三焦坚实之人,虽发其汗,未必周到,必须更汗通其怫郁。若误下之,则热证百出,遂至过经而成坏证,针药所不能制,势亦危矣。与水灌令阳散汗出,因而病愈,以其人荣卫素盛,故幸痊耳。然人之形脉,多有不同,设荣卫素弱,将奈之何?故叮咛云∶此愈非法治,医当谨持于汗下之先,勿使太过不及,乃为尽善。若不辨形脉之强弱,而凭臆汗下,必犯太过不及之戒,而伤人之荣卫矣。
一申治伤寒病不审荣卫素虚之律
脉濡而紧,濡则阳气微,紧则荣中寒。阳微卫中风,发热而恶寒。荣紧胃气冷,微呕心内烦。医以为大热,解肌而发汗。亡阳虚烦躁,心下苦痞坚。表里俱虚竭,卒起而头眩。客热在皮肤,怅怏不得眠。不知胃气冷,紧寒在关元。技巧无所施,汲水灌其身。客热应时罢,栗栗而振寒。重被而复之,汗出而冒颠。
体惕而又振,小便为微难。寒气因水发,清谷不容间。呕变反肠出,颠倒不得安。手足为微逆,身冷而内烦。如欲从后救,安可复追还?此见脉之濡而紧者,为阳气微,荣中寒。阳微卫中风,外则发热恶寒;荣紧胃中冷,内则微呕心烦。医不知其外热内冷,以为大热而从汗解之,则表里俱虚。客热浅在皮肤,紧寒深在关元,犹汲水灌其客热,致寒证四出,不可复救也。
前坏证汗下两误,针药莫制,与之以水而幸痊,以其荣卫素盛也。此一证荣卫素亏,虽不经下,但只误汗,误与之水,即属不救,然则证同脉异。不察其脉,但验其证,徒法不能行矣,过愆其可免乎?
一申治伤寒病不审阳盛阴虚之律
脉浮而大,浮为气实,大为血虚。血虚为无阴,孤阳独下阴部,小便难,胸中虚。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,法当卫家微。今反更实,津液四射,荣竭血尽,干烦不眠,血薄肉消而成暴液,医复以毒药攻其胃,此为重虚,客阳去有期,必下污泥而死。
脉浮而大,气实血虚,虽偏之为害,亦人所常有也。若此者,阴部当见不足,今反小便利大汗出,外示有余,殊非细故矣。设卫气之实者,因得汗利而脉转微弱,籍是与荣无忤,庶可安全。若卫分之脉,较前加坚实者,则阳强于外。
阴必消亡于内。所为小便利大汗出者,乃津液四射之征,势必荣竭血尽,干烦不眠,血薄肉消,而成暴液下注之证。此际安其胃,固其液,调和强阳,收拾残阴,岌岌不及。况复以毒药攻其胃,增奔迫之势,而蹈重虚之戒,令客阳亦去,下血如泥而死哉。伤寒病,阳强于外,阴亡于内之证最多,医不知脉,其操刃可胜数耶。
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强汗动其经血之律
跌阳脉浮,浮则为虚,浮虚相搏,故令气KT,言胃气虚竭也。脉滑则为哕,此为医咎,责虚取实,守空迫血,脉浮鼻中燥者,必衄也。
寸口脉浮,宜发其汗,谓邪在太阳荣卫间,未深入也。若至阳明,即在经之邪,以汗为大禁矣。设其人胃气充实,亦何必禁之。故邪入阳明,必诊趺阳足脉,趺阳脉浮,即是胃气虚馁,不可发汗,所以有建中之法创建中气,然后汗之,以汗即胃之津液也。津液不充,强发其汗,则邪与虚搏,其人必KT。若脉见浮而且滑。则其搏虚者,且转为哕,深于KT矣。此皆医者不察足脉之咎,强责胃气之虚,劫汗以取其实邪,致令胃中之守空,而逼其血外出。盖阴在内,为阳之守,胃中津液为阳,其不外泄者,赖阴血以守之,故强逼其津液为汗,斯动其所守之血矣。其外邪胜而鼻中燥者必衄,其不衄者亦瘀蓄胃中,而生他患也。此与误发少阴汗者,同科而减等。少阴少血,动其血则下厥上竭而难治;阳明多血,但酿患未已耳。
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误下伤其脾胃之律
趺阳脉迟而缓,胃气如经也。趺阳脉浮而数,浮则伤胃,数则动脾,此非本病,特医下之所为也。荣卫内陷,其数先微,脉反大浮,其人大便硬,气噫而除,何以知之?本以数脉动脾,其数先微,故知脾气不治,大便硬,气噫而除。今脉反浮,其数改微,邪气独留,心中则饥,邪热不杀谷,潮热发渴。数脉当迟缓,脉因前后度数如法,病者则饥,数脉不时,则生恶疮也。
趺阳足脉,以迟缓为经常,不当浮数。若见浮数,知医误下而伤胃动脾也,荣卫环转之气,以误下而内陷,其数脉必先改为微,而脾气不治,大便硬,气噫而除,此皆邪客于脾所致。即《针经》脾病者善噫,得后出余气,则快然如衰之谓也。邪热独留,心下虽饥,复不杀谷,抑且潮热发渴,未有愈期,必数脉之先微者,仍迟缓如其经常,始饥而消谷也。若数脉从前不改为微,则邪热未陷于脾,但郁于荣卫,主生恶疮而已。
附申治伤寒不可犯六经之禁
足太阳膀胱经,禁下。若下之太早,必变证百出。足阳明胃经,禁发汗,禁利小便。犯之则重损津液,脉必代结。足少阳胆经,禁汗禁下,禁利小便。汗则犯阳明,下则犯太阳,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,陷入阴中。太阳经一禁,阳明经二禁,少阳经三禁,此定禁也。至三阴经则无定禁,但非胃实,仍禁下耳。
附申治杂证不可犯时禁病禁药禁
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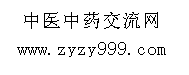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4:36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4:36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5:04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5:04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5:12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5:12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5:33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5:33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5:57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5:57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6:13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6:13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6:37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6:37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6:46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6:46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7:06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7:06 [只看该作者]


 加好友
加好友  发短信
发短信

 Post By:2011/4/19 9:47:25 [只看该作者]
Post By:2011/4/19 9:47:25 [只看该作者]
